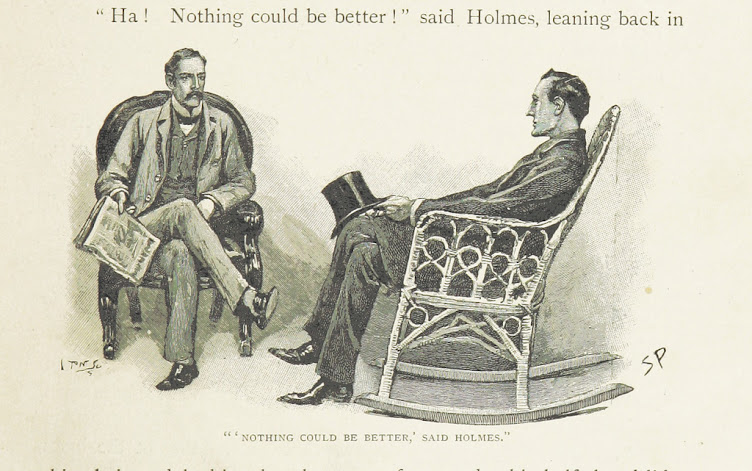福爾摩斯雖然被譽為名偵探的代稱,但卻好像很難期待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機巧謎團
發生在他身上,
舉凡血腥的分屍到鋼琴線扯來扯去之類,都不太常見。
舉凡血腥的分屍到鋼琴線扯來扯去之類,都不太常見。
可能是時代的問題,現代科技發達,連帶詭計也能變得更多樣化,有時就算不怎樣的詭計,配上ㄧ堆聽起來超難的物理化學名詞看起來就會了不起起來。
19世紀當然就沒這麼回事了。在那個最快的火車不知道有沒有現在普通車一半快的時代,連時刻表詭計都用不了呀…再來是原著本身的風格,原著並不是著重在殺人和詭計上,而是在案件的「奇」,福爾摩斯故事大概是這樣的:敘述奇妙事件的部份常常會花很多篇幅。福爾摩斯搜查的部份有時反而不多寫,然後說明的地方則可能會花一章。
現在的推理小說結構大多是人物介紹完就準備要死人了,然後進入長長的搜查(中間可能會再死人),最後則是說明。也就是說,福爾摩斯故事本身注重的不是”HOW”跟”WHO”而是”WHY”。
這基本上和現在讀者閱讀習慣是相反的,現在是莫名奇妙理由都可以殺人,只要殺得好(?)就好了。可能重故事不夠重謎題這一點會讓不少所謂推理迷詬病(之所以加”所謂”是因為有人看過幾本偵探漫畫就自以為自己是推理小說大師了)但我覺得,這一點反而是福爾摩斯能深植人心的原因也說不一定?
我ㄧ直不覺得《福爾摩斯探案》是推理小說,它應該是『以偵探為主角的小說』才是,它沒有厚重的謎題,也沒有無聊的社會批判,只有每本小說都應該有的「有趣的故事」。以19世紀的倫敦人眼光來看(話說在19世紀末的倫敦,私家偵探是很平常的職業的樣子),看著一個這樣特別的人,在自己所居住的無味的大城市中過著這麼精采又奇特的冒險生活,這是多麼的震撼呀。
謎要是被解開,就不再吸引人了。但奇妙的故事及讓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的吸引力卻是永久的。即使是現在也是一樣,即使知道《紅髮會》為什麼成立,知道《跳舞的小人》到底是誰畫的。但讀者卻從沒有看膩過這些故事。因為──福爾摩斯把冒險及不平凡帶到了我們平凡的生活中。
推薦《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給所有喜歡冒險和故事的人。
回到這本,
我實在是很想吐槽唐先生的導讀呀ORZ
看完之後實在是很難有想看這本書的欲望。
相當初我在機上看時本來就有點暈機的我看完後更暈了。
話說回來所謂導讀到底是什麼東西我不懂。但應該不是給那些專家炫學的地方吧?
還是唐先生只是想趁機介紹米蘭昆德拉囧?
我實在是很想吐槽唐先生的導讀呀ORZ
看完之後實在是很難有想看這本書的欲望。
相當初我在機上看時本來就有點暈機的我看完後更暈了。
話說回來所謂導讀到底是什麼東西我不懂。但應該不是給那些專家炫學的地方吧?
還是唐先生只是想趁機介紹米蘭昆德拉囧?
內容的話,基本上是各有勝場,
可以看到各式各樣不同詮釋法的福爾摩斯一直都是仿作最吸引人的地方了。
不過就像我之前所說的,可能不夠「推理」,但故事相當「有趣」
以單純的短篇故事來看也都很有功力。
其中也有寫《福爾摩斯對德古拉》的人的文章呢!
不過我最喜歡的是《福爾摩斯招喚的雙座馬車》,
用載到福爾摩斯的馬車夫的視點來寫的這篇文章真是讓人拍案叫絕!
而且非常爆笑!真的不看可惜!
另一個非常爆笑的文章(好啦!我承認我喜歡看好笑的東西囧>)在柯南道爾爵士的『側寫福爾摩斯』裡。
爵士的好友,《彼得潘》作者巴利先生所寫的『一對文學夥伴的奇遇』,
真是自嘲的極致!讓人不得不對他脫帽致敬。
這裡有別的網友的心得介紹
這裡